■崔凱
關于咖啡、甘蔗、胡椒、辣椒和棉花的通識書籍,敘事時間軸大約是500年——這些物種主要是在“地理大發現”后走向世界的。
相比之下,谷物是農業版圖中的“主角”,是人類最悠久的馴化物種,有著1萬年的歷史。
 (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
每學期結束上海交通大學的MBA課程時,我都會給同學們朗誦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其實過去4年,我的確是在“關心糧食和蔬菜”,埋頭寫這本20萬字的《谷物的故事》。今天,蒸了4年的“饃”終于呈現在大家面前,它的讀者可以是任何熱愛自然、歷史和生活的人。
法國博物學家法布爾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們在戰場上殞命,歷史卻對這些戰場大加宣揚;我們在耕地里繁榮,歷史卻對這些耕地充滿輕蔑、不愿提及;國王的私生子都能在歷史上留名,而小麥的源頭卻無人知曉。人類就是如此愚蠢。”時至今日,能說出小麥、水稻、玉米、大豆發源地的人依然很少。
在很多人眼中,谷物只是包裝袋中的各種糧食、天天需要吃的食物。因此看到這個書名,難免會想谷物能有啥故事。
可是,多數人不知道的是:為什么最終成為人類主食的是谷物,而不是水果或者肉類?為什么西方人喜歡吃面包,中國人喜歡吃饅頭?人類歷史上發生過哪些大的饑荒?為什么今天很多食物沒有以前好吃了?谷物如何成為全球貿易、生物能源和氣候變暖的主角?等等。本書試圖“以谷物的視角,看人類的歷史”。
先作個簡單對比,電燈的歷史有100多年,火藥的歷史有1000多年,而谷物的歷史則有1萬多年。
13000年前,地球突然遭遇了一次冰期,氣溫驟然下降了8℃,相當于福州的年均溫度變得和北京差不多。這場冰期持續了約1200年,生態系統像“紙牌屋”一樣崩潰了,考古遺存中野草種子數量開始增加。很多學者推測,冰期帶來的生存壓力,迫使人類吃起了以前看不上眼的草籽,開啟了谷物馴化道路。
學會種植谷物以后,人類才有了定居生活,有了職業劃分,有了文字和藝術,形成了城市和國家。或者可以說,人類文明的開啟只是一場絕處逢生的“意外”。有了食物保障,人類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地球人口從1萬年前的幾百萬,激增到今天的近80億。
對我來說,如果一定要說出點“命中注定”的事,就是今天出版了這本書。
1970年,我出生在東北農村,房前屋后就是綿延幾十里的農田。小時候家里沒有電視,更沒有今天的手機和網游,放學后要幫父母割草、挑糞,也常在田野里捉蜻蜓、逮蟈蟈、掏鳥窩,見證了谷物的春華秋實。
1988年,我考入吉林農業大學農學系,至今記得當年邁入大學校門時的情景——那天陽光燦爛,我拎著用粗麻繩捆起的行囊,新奇地四處張望著。1997年,我在江南大學食品工程專業獲得第一個博士,老家有位長輩曾問我:食品工程博士畢業以后,是不是相當于“一級廚師”?1999年,我又在華東師范大學心理學系讀了第二個博士,浸染了文科的思維。
工作這些年,我主要從事投資和咨詢職業,到各地調研過數百家企業,還兼任了多家農業上市公司的獨立董事。這些經歷在我的腦海里逐漸勾勒出一幅“谷物產業全景圖”。
2018年,我到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做訪問學者,選修了人類學系的《人類史大變遷》課程,人類學的視角和全球化的視野給我很大觸動。
一些關于咖啡、甘蔗、胡椒、辣椒和棉花的通識書籍,敘事時間軸大約是500年——這些物種主要是在“地理大發現”后走向世界的。相比之下,谷物是農業版圖中的“主角”,是人類最悠久的馴化物種,有著1萬年的歷史。
中國是主要的谷物起源地之一,糧食安全在今天更是重中之重。然而我在網上檢索了一下,居然沒有發現谷物歷史的通識讀本,這讓我感到驚訝。
于是萌生了一個想法:能不能站在谷物的視角,寫一本1萬年的人類史書籍?那一天,我因為這個想法激動到深夜。就這樣,我開始了“自作多情”的創作。
在我讀過的一些專業農史著作中,發現有兩個現象:其一,很多研究局限于考古和歷史領域,缺少與生物、氣候、文化、生活、經濟、貿易和文明等研究領域的融會貫通。其二,很多研究都選擇了一個“1厘米寬”的課題,挖到“1米深”。有些成果很有敘事性,然而被寫成了晦澀的學術論文,發表在學術刊物上以后,就被束之高閣,無人問津。
與“探幽發微”的學術風格不同,我更注重內容的廣度。我覺得自己很像拾荒者,搜集了不同學科領域的“邊角料”,努力將這些碎片“小故事”拼接起來,嘗試著勾勒出一幅“一米寬”的“大歷史”畫卷。
而在寫作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擁有一些“雜食者”的優勢。
其一,年少時的鄉村生活經歷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田野調查”。對我來說,谷物不僅是書本上的文字,而且是厚重的人生記憶。我心中經常涌動著一份激情,寫到“結束語”一節,甚至直接寫出了“遠去的鄉村記憶”。
其二,從本科到博士,我學習了多個專業。這種從“田野”到“餐桌”、從理科到文科的學習經歷讓我有了多元化的視角。有時看到好的文章,不僅會作為參考文獻,我還會發郵件向作者求教。大家深入交流,互通有無,不僅拓寬了視野,還成為了朋友。
其三,多年的農業調研使我跳出書本,更多地融合社會現實。每每遇到專業難題,一個電話聯系到“三教九流”的良師益友,就能獲得真實、硬核的信息。有些資訊甚至是學術研究的盲區,只有“實踐者”才能說得清楚。
這幾年,我曾在北京、上海、杭州、青島等地作科普演講,也寫了很多篇科普網文,收獲了超過1000萬人次的瀏覽量。讀者留言中有很多建議和質疑,讓我體會到科學傳播的社會意義。
在學術圈里,有人覺得做科普是“不務正業”。其實,一篇影響因子為10的學術論文和一篇10萬+瀏覽量的公眾號文章,哪個對社會更有貢獻?見仁見智。
做科普的人往往是有情懷的,這種情懷在只關注文章數量的學術圈里彌足珍貴。
為了“戳中”讀者的興趣點,我和朋友做了一次“公眾關注的農業”社會調查,覆蓋了31個省份的242座城市——很少有作者會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將調研結果寫成了一篇論文,發表在Science of Food刊物上。調查數據令我驚訝——人們依舊關注著農業,只是這種關注已經從“鋤禾日當午”升級到“舌尖上的中國”。
圍繞這些話題,我開始重建全書的架構,原先的第一稿和第二稿分別站在農業和物種的視角,現在第三稿則站在歷史的視角。
我愿意寫有情感、有溫度、能夠讓人們讀懂的東西,也希望能為讀者帶來一份輕松和愉悅。鄉土是我與生俱來的一塊胎記,骨子里我仍是那個手拿鐮刀在田野中割草的少年,有著自然蠻性。
感謝袁闊成、劉蘭芳等藝術家,從小我就依在收音機前聽他們的評書,浸染了貼近生活的語言風格。感謝電腦里的3000首歌曲,這些音樂一路陪伴著我成長。寫作時旋律響起,和著鍵盤聲,文思涌動,天馬行空。
30年前,《平凡的世界》和《文化苦旅》在我心里埋下了鄉土情懷和文化散文的種子,也影響到這本書的風格。
書中穿插了一些趣聞逸事,比如秦朝人的食譜、清朝的人口暴增、藍罐曲奇的源頭等;還有蘇格拉底、康熙、孟德爾的掌故,梵高、莫奈、齊白石的畫作,海子的詩,以及羅大佑、童安格的歌……
這本書于我還是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因為初衷是將多個領域的谷物資訊融合在一起,梳理出人類歷史和文化的變遷,但如此宏大的敘事非我能勝任。現在只能算“勉力畫了一個葫蘆”。
因此中國科學院院士許智宏對這本書的肯定給了我莫大的鼓勵,他說:“谷物不僅是田野中的植物,更是為地球上的人類提供了主要的食物,由此奠定了人類農業文明的基石。《谷物的故事》收集了豐富的史料素材,將物種、農耕、歷史、經濟、飲食和生活融合在一起,伴隨農業的變化和發展,勾勒出過去1萬年的人類史,是一本適于公眾閱讀的很好的通識讀物。”
我很喜歡“老樹畫畫”的一句話:“我像花兒一樣開過了,我像麥子一樣飄過了,我像自己一樣活過了。我孤坐于天地的盡頭,面對著田野微笑。”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MBA課程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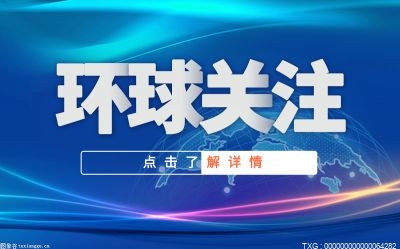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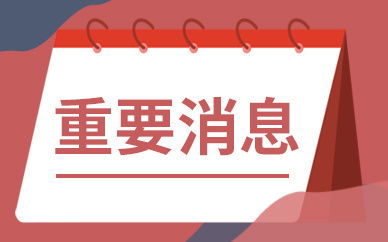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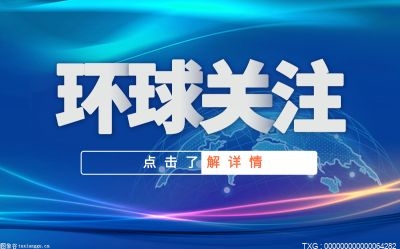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