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換來讀者的一句“這書有用”,需要多少付出?為了這句話,一個人歷時15年,跑了450萬行代碼,用一本重達2.8公斤、字數多達384.7萬字的“康熙字典”給出了答案。這本書就是北京林業大學林學院教授劉琪璟的著作《中國植物拉丁名解析》。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毋庸置疑,本書是中國植物學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因而被稱為“植物分類學的康熙字典”,可作為《中國植物志》的輔助參考或補充。
植物的學名,也就是國際上通用的名稱,一般由最初發現該植物的人用拉丁語命名,以便統一稱呼。
植物拉丁名多數為復合詞,有豐富的含義,反映植物的形態特征、生物學特性、生態習性、使用價值,還有不少豐富的歷史文化要素,如古代地名、古代民族、地方土名、重大事件、神話人物等。
但是,由于拉丁語并非一門通用語言,不要說讀者,就連大多數植物學研究者理解起來都異常困難。鑒于此,作者對植物拉丁名的構詞進行拆分“破譯”,詳細剖析各種構詞成分的含義,解釋構詞規則。
該書把表面上看著晦澀難懂的拉丁名復合詞拆解成最基本的構詞單元,對植物拉丁名進行“基因解碼”,將其背后記載的人物介紹勾畫出的植物分類學的發展歷史,以及世界各國學者的貢獻一一展開,讓讀者了解到單詞背后包含的生動元素,集學術意義與趣味性于一體。
同時,該書讓植物研究者在不知不覺中記住植物拉丁名及其特點,掌握更多的植物學拉丁語詞匯,有利于提高科技工作者在植物分類學上的基本能力。
該書涉及的植物拉丁名是以《中國植物志》為核心的。進行構詞解析的對象是《中國植物志》記錄的全部維管束植物及近年來發現的新種、新記錄和外來物種的拉丁名。
此外,該書對《中國植物志》中存在的構詞錯誤、拼寫錯誤、印刷錯誤等進行了訂正,采用了經典《中國植物志》初版所用分類單位名稱,可以作為《中國植物志》這本植物分類領域最權威、最經典的著作的輔助參考或補充。
作為一本工具書,《中國植物拉丁名解析》為了方便讀者使用,在排版上下足了功夫。因采用了《中國植物志》初版所用分類單位名稱,有利于讀者查證;在檢索上編排了多途徑檢索方式,包括拉丁名檢索、中文科屬名檢索、種加詞檢索,更加實用;對于在不同植物名稱中重復出現的詞,作者則利用數據處理能力“不厭其煩”地反復解釋,使得該書更加完整,使用起來更為方便。
起初,劉琪璟只是想建立一個關于自己研究區域的植物拉丁名的術語單詞本,用于記憶拉丁名。但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他發現該領域涉及學科范圍廣且復雜,相關資料并不多,國內外甚至沒有關于植物拉丁名的系統性解析。
與此同時,劉琪璟在授課過程中,以及與同行交流時,越發感受到這樣一個術語單詞本的必要性。于是,他產生了一個沖動,就是把中國的植物學名都收錄進來進行全面解析,他的術語單詞本應該為更多人帶去便利,讓更多植物學研究者受益。
有了這樣一個想法之后,劉琪璟立刻付諸實踐。由于手頭的資料少之又少,市面上相關的資料也并不齊全,他就去舊書網等四處收集資料,翻閱植物分類學中最原始的文獻。除了中文之外,還要找海量的英文、日文等外語資料,“把能收集到的全部收集到了”。
這一工作不僅需要植物學專業知識,對外語的要求也非常高。在梳理與甄別詞匯時,他會通過發音判斷一個詞的語言來源,提出源頭假設,進而翻閱資料查證。每一個詞的解析工作都需要一點一點進行推敲、確認,碰到拿不準的非專業問題,他會在線上線下查閱國內外資料,或請教相關領域專家,力求每一個知識點的精準與可靠。
解析工作本身是繁雜的,但作者依然會為了其中的一個詞反復查證,有時考證幾天就為了給出一個準確的解釋。“哪怕花三五天也沒關系,只要能解決就好,我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了,其他人就不用再費時間了。”劉琪璟如是說。
除了解析本身的困難,過程中還會遇到數不勝數的挫折。有時候碰到電腦崩潰,一兩個月的工作就白費了。為了解決編排上的問題,他還自學了代碼,交付成稿時用來檢查錯誤的代碼高達400多萬條。工作起來,忙到后半夜是常有的事兒。他說:“看到讀者評價說‘這書有用’,我就覺得值了。”
當讀者拿到這本重達2.8公斤的工具書時,映入眼簾的是全面、詳細的知識點與整齊細致的排版,背后卻是作者15年來默默的無私付出與攻堅克難。
不少讀者評價此書“很實用”“一冊在手,中國植物拉丁名盡知”,許多學校圖書館也將此書收為館藏,豐富文獻收藏結構與知識寶庫,為植物學讀者提供便利。 (宋和 楊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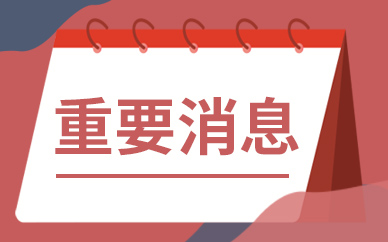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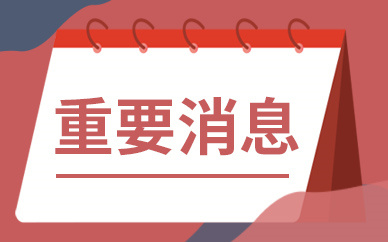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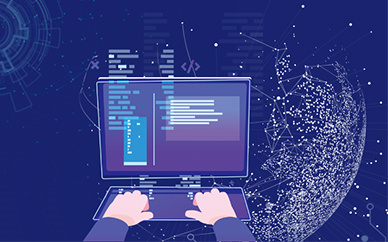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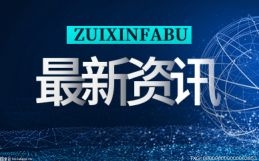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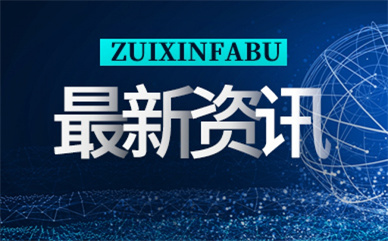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
營業執照公示信息